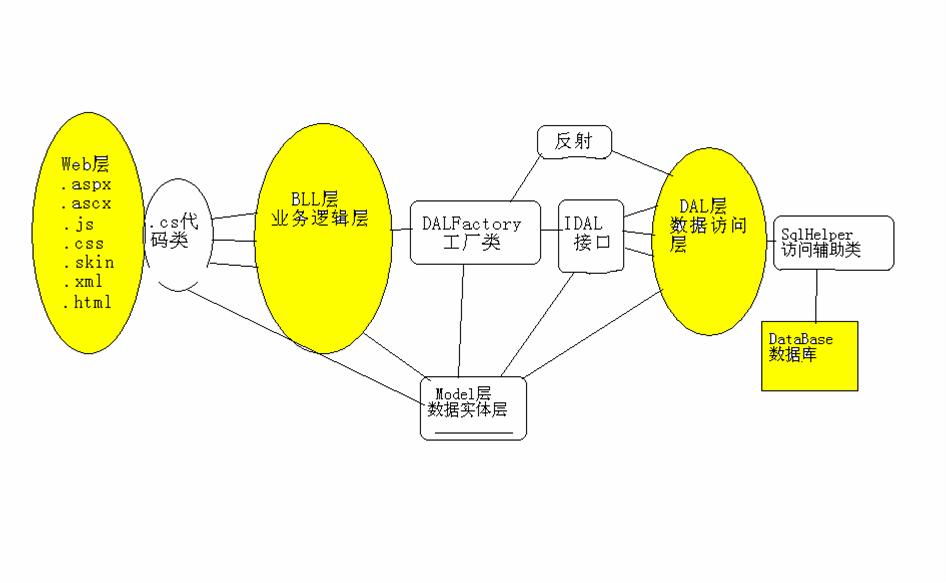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今年来深圳知名信托私募机构目前收入普遍在数百万到数千万元之间,私募基金经理收入大约占机构收入很大一部分。据成都当地媒体报道,成都一位私募人员去年年收入达到1900万元。经常有深圳的资深股民流传“谁谁去年做私募赚了上亿元”。
一位知名私募人员透露,私募基金经理收入要分收入构成。单单算私募基金管理收入应该难有上亿元收入,不过很多私募经理算上自己的投资收入,最终总收入超过1亿元的私募基金经理还是大有人在。
以管理资产规模较大的晓杨投资公司为例,晓杨投资和平安信托合作发行了两只信托私募产品。去年10月17日,“平安晓杨一期”募集了1.21亿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已经实现累计收益率133.62%。
今年2月28日,“平安晓杨二期”又募集了1亿元,目前已经实现累计收益率46%。私募机构收取投资收益的20%作为投资顾问费,晓杨投资收入大概在4000万元左右。晓杨投资团队核心成员大概在六七人之间,各人收入状况也应该在数百万元到千万元左右,原君安证券总裁杨骏是晓杨投资负责人,其收入状况应该在千万以上。
此外,深圳私募机构中天马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的康晓阳、明达投资的刘明达、赤子之心的赵丹阳由于管理的私募基金资产规模较大,收入状况也应该有数千万元。但部分信托私募基金发行时间较短,加上发行规模偏小,私募基金经理今年以来的收入应该只有几百万元。
激励手段成公募最大短板
即使管理资产已经接近1500亿元的南方基金,也面临着人才问题。作为成立时间最长的基金公司之一,南方基金为业界培育了众多人才:如李旭利、王宏远和苏彦祝等。这批年轻人是南方基金一手培养,但其中李旭利早已从投资总监任上离开,辗转投入私募。
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近日说,“在一次持有人大会上,一位老客户跟我如数家珍地谈起南方基金这几年离开的基金经理,我告诉他没有必要担忧。这是现实,但未必是坏事。尽管公募和私募都需要优秀的人才,但是公募基金更需要把优秀的人才组织成和谐的团队。”
公募基金的人力资源定位,取决于其自身的定位。公募基金提供的是一种收益平均化的基础投资产品,与私募基金的高风险高收益相去甚远,因而也就没有可能实现私募基金的激励手段。就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而言,正是激励手段使得私募基金更具人才附着力。
在2000年至2005年的熊市中,券商全行业萎缩,而基金公司,特别是有封闭式基金的大公司则“日子相对好过”。这段时间里,基金公司是一个“人才洼地”,尚不存在流失问题。
但是洼地总是相对的,当下一个洼地出现时,基金公司的“洼地效应”也就随之消失。2006年启动的牛市伴随着证券市场私募基金的重新活跃,深圳、上海的一批私募基金在本轮牛市中的业绩达到了令人惊羡不已的地步。
这些运作私募基金的投资公司,通常基金经理、研究员、财务和行政加起来不超过十几个人,甚至更少,其单个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对于公募基金来说也算不上庞大。但是一只2亿元规模的私募基金,在顶尖的操盘者运作下甚至会有几倍的收益,提取20%的业绩报酬后就是上亿元的收入。这个数量级,基本相当于业界最大的基金公司去年全年的净利润。
高良玉说,“公募(股票型)基金仅仅提取大约1.5%的管理费,它的定位就是为公众提供一项基本理财服务,收益目标也仅仅是跑赢业绩基准。私募基金针对的是高端客户,提供的是高收益的产品,因而也就对应了高额业绩报酬。不宜对公募基金有私募基金那样的预期。”
在他看来,公募基金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流向私募的可能性很大。“在国外也是这样的情况。公募基金接受严格的监管,限制很多,高风险的个股不能参与,复杂的衍生工具不能使用或者很少能用,能力强的基金经理没有施展拳脚的余地。”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私募能提供基金经理2000万元一年的报酬,而且几乎对个人投资没有限制,公募的平均收入却是30万~100万元,这种薪酬的差距是无法平衡的。
不过收益总是与风险随行。从公募出走到私募,对于基金经理而言是一次慎重的抉择。在私募基金,从销售到服务,从研究到投资,各个环节他都需要有独当一面的魄力和能力,达到如此境界者毕竟凤毛麟角。
打造团队应付个体流失
高良玉说,“这两天媒体似乎有点过度渲染悲观情绪。公募基金人才流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是客观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公募基金就此走入低谷。”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募基金需要审时度势,寻找适合自己的人才战略定位。高良玉说,在南方基金,公司统一管理下倚重团队投研决策的模式,早已取代依靠单个“明星基金经理”的传统路径。
“基金经理个人的不足,可以通过团队化的投资管理来弥补。”高良玉介绍说,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事实上在整个投资决策过程中只负责最后的头寸管理、时机把握和个股遴选,在此之前,宏观判断和行业选择都是由公司的投研团队完成。
传统模式下,基金公司的研究员只起到辅助作用,基金经理甚至经常不理会研究员的投资建议,但是南方基金赋予研究员一定比例的投资决策权,从而使其也参与到基金管理中。 “这有两种好处,一是对研究人员有激励,二是对基金经理形成一种竞争压力。”高良玉说。
另一方面,改革现有制度的不合理因素,也能改善公募基金的用人环境。公募基金从一开始就接受着严格的监管,基金经理被明确要求不能进行证券投资,连持有自己管理的基金也不被允许。一位业内人士说,“除了国债和银行存款,基金经理包括他(她)的亲属,都被'剥夺’了投资的权利。”
高良玉说,“尽管我们不可能有私募基金那样的激励方式,但是改变现有制度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仍然能够带来正面效果。”他认为,应当将个人投资权利还给基金经理。“我们最担心的是内幕交易,但是通过申报制度和公司的内部控制,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让基金经理以一定比例认购自己管理的基金,与持有人'同甘苦’。”
高良玉说,“除此之外,还应当把他们从短期的业绩排名中解脱出来,我们的市场还是初期阶段,大家喜欢搞净值排名,但是在成熟市场都是看长期资产增值的,短期排名并没有意义。”他表示,南方基金总体是按照年度考核投资人员。
今年南方基金正在筹备发起QDII基金,招募海外人才的计划也已提上议事日程。高良玉表示,“在业务推向海外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国内基金公司与国际接轨的人力资源体系。
一位知名私募人员透露,私募基金经理收入要分收入构成。单单算私募基金管理收入应该难有上亿元收入,不过很多私募经理算上自己的投资收入,最终总收入超过1亿元的私募基金经理还是大有人在。
以管理资产规模较大的晓杨投资公司为例,晓杨投资和平安信托合作发行了两只信托私募产品。去年10月17日,“平安晓杨一期”募集了1.21亿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已经实现累计收益率133.62%。
今年2月28日,“平安晓杨二期”又募集了1亿元,目前已经实现累计收益率46%。私募机构收取投资收益的20%作为投资顾问费,晓杨投资收入大概在4000万元左右。晓杨投资团队核心成员大概在六七人之间,各人收入状况也应该在数百万元到千万元左右,原君安证券总裁杨骏是晓杨投资负责人,其收入状况应该在千万以上。
此外,深圳私募机构中天马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的康晓阳、明达投资的刘明达、赤子之心的赵丹阳由于管理的私募基金资产规模较大,收入状况也应该有数千万元。但部分信托私募基金发行时间较短,加上发行规模偏小,私募基金经理今年以来的收入应该只有几百万元。
激励手段成公募最大短板
即使管理资产已经接近1500亿元的南方基金,也面临着人才问题。作为成立时间最长的基金公司之一,南方基金为业界培育了众多人才:如李旭利、王宏远和苏彦祝等。这批年轻人是南方基金一手培养,但其中李旭利早已从投资总监任上离开,辗转投入私募。
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近日说,“在一次持有人大会上,一位老客户跟我如数家珍地谈起南方基金这几年离开的基金经理,我告诉他没有必要担忧。这是现实,但未必是坏事。尽管公募和私募都需要优秀的人才,但是公募基金更需要把优秀的人才组织成和谐的团队。”
公募基金的人力资源定位,取决于其自身的定位。公募基金提供的是一种收益平均化的基础投资产品,与私募基金的高风险高收益相去甚远,因而也就没有可能实现私募基金的激励手段。就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而言,正是激励手段使得私募基金更具人才附着力。
在2000年至2005年的熊市中,券商全行业萎缩,而基金公司,特别是有封闭式基金的大公司则“日子相对好过”。这段时间里,基金公司是一个“人才洼地”,尚不存在流失问题。
但是洼地总是相对的,当下一个洼地出现时,基金公司的“洼地效应”也就随之消失。2006年启动的牛市伴随着证券市场私募基金的重新活跃,深圳、上海的一批私募基金在本轮牛市中的业绩达到了令人惊羡不已的地步。
这些运作私募基金的投资公司,通常基金经理、研究员、财务和行政加起来不超过十几个人,甚至更少,其单个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对于公募基金来说也算不上庞大。但是一只2亿元规模的私募基金,在顶尖的操盘者运作下甚至会有几倍的收益,提取20%的业绩报酬后就是上亿元的收入。这个数量级,基本相当于业界最大的基金公司去年全年的净利润。
高良玉说,“公募(股票型)基金仅仅提取大约1.5%的管理费,它的定位就是为公众提供一项基本理财服务,收益目标也仅仅是跑赢业绩基准。私募基金针对的是高端客户,提供的是高收益的产品,因而也就对应了高额业绩报酬。不宜对公募基金有私募基金那样的预期。”
在他看来,公募基金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流向私募的可能性很大。“在国外也是这样的情况。公募基金接受严格的监管,限制很多,高风险的个股不能参与,复杂的衍生工具不能使用或者很少能用,能力强的基金经理没有施展拳脚的余地。”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私募能提供基金经理2000万元一年的报酬,而且几乎对个人投资没有限制,公募的平均收入却是30万~100万元,这种薪酬的差距是无法平衡的。
不过收益总是与风险随行。从公募出走到私募,对于基金经理而言是一次慎重的抉择。在私募基金,从销售到服务,从研究到投资,各个环节他都需要有独当一面的魄力和能力,达到如此境界者毕竟凤毛麟角。
打造团队应付个体流失
高良玉说,“这两天媒体似乎有点过度渲染悲观情绪。公募基金人才流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是客观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公募基金就此走入低谷。”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募基金需要审时度势,寻找适合自己的人才战略定位。高良玉说,在南方基金,公司统一管理下倚重团队投研决策的模式,早已取代依靠单个“明星基金经理”的传统路径。
“基金经理个人的不足,可以通过团队化的投资管理来弥补。”高良玉介绍说,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事实上在整个投资决策过程中只负责最后的头寸管理、时机把握和个股遴选,在此之前,宏观判断和行业选择都是由公司的投研团队完成。
传统模式下,基金公司的研究员只起到辅助作用,基金经理甚至经常不理会研究员的投资建议,但是南方基金赋予研究员一定比例的投资决策权,从而使其也参与到基金管理中。 “这有两种好处,一是对研究人员有激励,二是对基金经理形成一种竞争压力。”高良玉说。
另一方面,改革现有制度的不合理因素,也能改善公募基金的用人环境。公募基金从一开始就接受着严格的监管,基金经理被明确要求不能进行证券投资,连持有自己管理的基金也不被允许。一位业内人士说,“除了国债和银行存款,基金经理包括他(她)的亲属,都被'剥夺’了投资的权利。”
高良玉说,“尽管我们不可能有私募基金那样的激励方式,但是改变现有制度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仍然能够带来正面效果。”他认为,应当将个人投资权利还给基金经理。“我们最担心的是内幕交易,但是通过申报制度和公司的内部控制,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让基金经理以一定比例认购自己管理的基金,与持有人'同甘苦’。”
高良玉说,“除此之外,还应当把他们从短期的业绩排名中解脱出来,我们的市场还是初期阶段,大家喜欢搞净值排名,但是在成熟市场都是看长期资产增值的,短期排名并没有意义。”他表示,南方基金总体是按照年度考核投资人员。
今年南方基金正在筹备发起QDII基金,招募海外人才的计划也已提上议事日程。高良玉表示,“在业务推向海外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国内基金公司与国际接轨的人力资源体系。